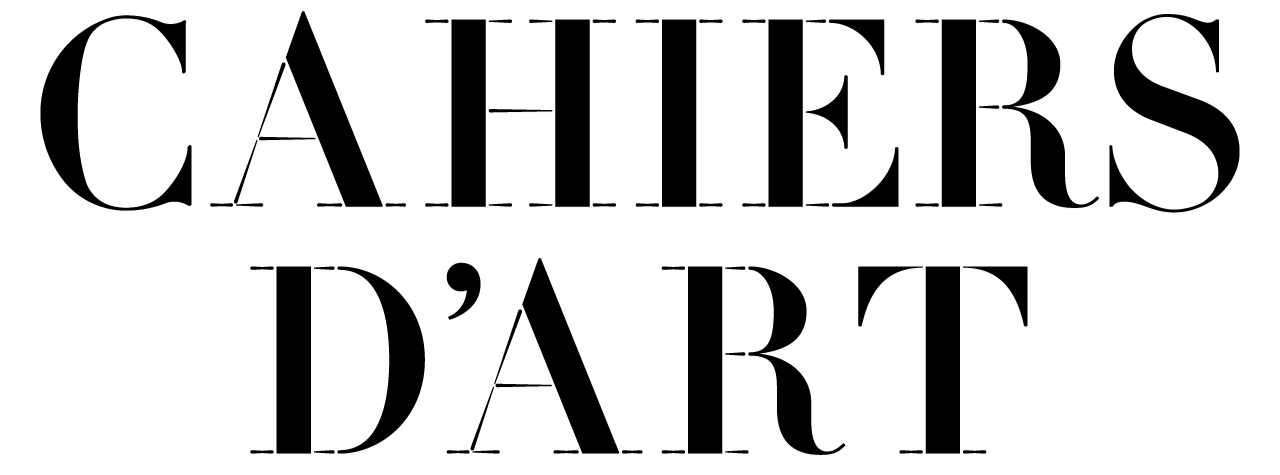文章: 波尔·塔布雷:帽子与狩猎

波尔·塔布雷:帽子与狩猎
《艺术笔记》荣幸地宣布,将于 2025年10 月 18日至 12 月 20 日在巴黎龙街 14 号和 15 号的两家画廊举办波尔·塔布雷的《帽子与狩猎》展览。
埃尔·格列柯笔下被剥皮的人物,苏巴兰画中“静静滑过死者石板路”的僧侣,戈雅的噩梦——它们在普拉多博物馆的走廊里一一出现。戈雅,尤其是年老的戈雅,他的眼睛永远充满恐惧,因为他目睹了太多的恐怖;戈雅,“一位精通英国顶级绘画中灰色、银色和粉色运用的大师,[却训练有素]用膝盖和拳头在可怕的焦油黑中作画”。他们把他放在博物馆最深处,在一个黑色绘画的房间里,那里所有的骄傲都被压制,提醒我们,某个西班牙人的思想和生活是多么深陷于黑色之中。就在几条街之外,人们在一家名为 Dolores(意为“悲伤”)的酒吧里互相问候,彻夜畅饮;再往前走,从另一个拉着窗帘、半开着门的房间里,传来弗拉明戈歌手的歌声,打破了为他营造的寂静。
正是在西班牙——一个“向死亡敞开大门”的国家,死神倚窗而立时会受到人们的欢呼,而当死神疲惫不堪时,人们会把他背在背上——波尔·塔布雷特尝试了石版画创作。他是在弥漫着马德里传说和幽灵气息的空气中,在精神大师戈雅(他必须被这样称呼)的注视下,怀着向戈雅致敬的意图进行创作的:首先,也是最重要的,是追捕——这堪称一种“圣经传统”,也是治理世界的一种方式,尤其是在需要控制世界的时候。
这样的现实不可能逃过埃利亚斯·卡内蒂的眼睛,他大胆地问道:“如果一切都能绝对且永远地保密,谁会杀害谁?”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,而这个问题也的确值得用几块石头来呈现——正是这些石头构成了波尔·塔布雷的《托内尔爸爸的故事》 。这些版画的主人公默默地收集了知己们最可怕的忏悔,并将它们公之于众,最终却被判流放,在虚空中无尽地徘徊。一旦所有本应被封存在沉默承诺中的秘密被释放,阴影之舞便开始了,各种恶习得以肆意横行,杀戮或死亡也变得可以毫不犹豫地发生。
在一种充满阴谋的、炼狱般的氛围中——或许是猜忌的弥漫——这十二幅版画描绘了十二个场景,诉说着一场人人为敌的战争。它们讲述了一场猎杀,每个人都是彼此的猎物,而上帝却无能为力地袖手旁观,任由他的孩子们自相残杀。最终,太阳是否依旧照耀,地平线是否依然升起夺取光明,都变得无关紧要,因为彼岸似乎已经与尘世失去了联系。这些版画并非天真地想要触碰恩典,而是从街巷深处涌现,那里战火纷飞的阴影悄然掠过,它们毫不在意自己应该加入军队还是民兵,因为毕竟,每个人都可能是叛徒。它们走向深渊,它们挖掘,它们掘穴。它们之所以有意义,是因为姿态与思想、技法与内容之间最终形成了一种连续性,也因为版画有着笔触所无法企及的内在逻辑。
石版印刷唤起空虚与偶然;它只在不经意间做出一些事先未曾预告的举动,才勉强同意妥协。它要求人们为每一个清晰的意图而哀悼,因为试图展现反而会隐藏,试图隐藏反而会暴露:正如波尔所说,绘画的“X光”——它的骨架——就此显现。线条晕染,污渍浮现,“悲伤的西班牙”的所有黑暗似乎都顽强地从底层涌出。
的确,在这里,肮脏丑恶毫不掩饰。在宗教裁判所时期,刽子手的房子被漆成红色,“因为他必须用红色标记自己的巢穴和身份,以震慑世人”,于是,恐怖便以宗教裁判官们黑色的、长着角的头颅的形式,肆无忌惮地招摇过市。
然而,如果仅仅从这些版画、绘画、素描中看到失败的悲观主义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歌颂死亡,与死亡共舞。 ——将其具象化,拥抱它,并像西班牙传统那样热情地拍打它的后背——归根结底,也是对卡内蒂在回答他那充满杀意的提问时所作回应的另一种肯定:“最好活得如此淋漓尽致,以至于无人能够真正死去。”这的确关乎那些永不消逝的幽灵;这关乎灵魂,关乎幸存者。

图片来源:Pol Taburet,《Papa Tonnerre的故事》,2025年,石版画,由艺术家及Mendes Wood DM画廊(圣保罗、布鲁塞尔、巴黎、纽约)提供。